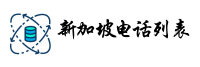在学校,我确实戴过眼镜,但盲人没有戴任何装备,比如白手杖、盲文名片,这些都是后来才有的。然而,我却成了无情欺凌的源头。我记得自己害怕一些平凡的事情,比如不小心把铅笔掉在地上,因为我不得不跪下来,羞愧得冒冷汗,班上的男生嘲笑我,叫我“瞎子”,而我用手指在地上摸索着寻找掉落的书写工具。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因为几个世纪以来,残疾儿童被关在机构里,而非残疾儿童则被教导要害怕和低估他们。这些对残疾根深蒂固的恐惧至今仍然存在,并被用来伤害残疾儿童。
尽管美国只有 10 项研究将残疾与
校园欺凌联系起来,但根据 2009 年的一项研究 ,残疾儿童遭受欺凌的 哥斯达黎加电话号码库 可能性是非残疾同龄人的两到三倍。 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 2019 年的一项最新分析 发现,除了外貌、种族/民族、性别、性取向和宗教信仰外,残疾也是学生报告的最常见的欺凌原因之一。欺凌的负面影响包括学校成绩下降、旷课率上升和毕业率下降等。
这些数据对我来说并不意外,因为它反映了我自己的童年。这就是学校延续 残疾歧视文化的方式——并且需要强有力的民权法来实现让残疾儿童获得与非残疾同龄人相同的教育机会这一简单步骤。
值得庆幸的是,对于新一代残疾学生来
这种现实正在改变,我们可以开始看到一个由在残疾积极教育中成长的人们重塑的世界。
宾夕法尼亚州残发有利于残疾的课程,向儿童传授各种形式的残疾,以及如何尊差异。残疾作家正在出版《 我们一起行动》 和 《滚动战士》
而这仅仅是个开始。各州、地方和学校董事会必须要求将残疾问题纳入 K-12 课程。由于 IDEA,学生有机会和权利与非残疾同龄人一起学习,他们应该在所接受的教育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他们不应该独自探索这些发现——非残疾儿童应该与他们并肩作战,建立残疾意识,并找到创造性的方式共同努力,确保每个人都能融入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这成 香港领先 疾平等与教 基础,那么长大后成为建筑师的孩子就不太可能忘记建造坡道并使其变得美丽;成为医生的高中生更有可能表现出同情心并为残疾患者提供住宿;非残疾政府领导人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更有可能考虑残疾问题。即使在遭受欺凌和被排斥的孤独之后,我相信这个新世界是可 “走向消除公民身份? » 能的,因为知识是修复我们对异类根深蒂固的恐惧的有力工具。